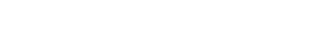人物名片:罗俊才,1919年出生于山西太原,1941年进入延安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学习俄语。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主任,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务长,1984年正式离休。
他是北外的首批学员,经历了学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时期,作为曾经的教务长,他见证了北外从无到有,发展壮大的艰辛历程。许多刻骨铭心的回忆,并没有在时间的长河中失了颜色,在与罗俊才老师的交流中,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。
艰苦环境中的“速成”教学
谈起学习经历,罗俊才印象最深的是战争年代学校的特殊烙印。北外的前身——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,早期是从军事学院中分离出来的。由于学校创建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,因此语言的学习,更多是为当时的军事斗争服务,这就对培养人才的速度提出了要求。因此,与今天不同,早期外语教学方法更多追求的是“速成”,强调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以致用。但同时,今天北外的一些雏形在很多方面已经体现出来。
比如当时的分班,一共有五个班,每个班的学生二十到三十人不等,实行着军事化的管理。外语学校特色的小班教学在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显露雏形了。
学校也很重视分层次教学,五个班里面分为“高起”和“低起”班。前面三个班的学生在此前都或多或少接触过俄语,属于高起班;四、五班都是零基础的年轻人,则属于低起班。
学校的老师,当时称为“教员”,一共只有七个人。老师都曾有过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生活的经历,来源也是国际化的,除了中国人,还有朝鲜人,越南人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们都不是专职的教师,除了教书之外每个人还有自己的革命工作。
虽然从今天的标准看,可能很多老师的教学还够不上专业,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值得尊敬,在艰苦的条件下,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热情,释放最大的潜力,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。没有教材,甚至没有任何参考资料,他们开动脑筋,结合实际,自己编写。据罗俊才老师回忆,许多老师还是当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,以至于课程安排很多时候是见缝插针。
学校当时可以说几乎是一穷二白,白手起家。上课没有专门的教室,经常是挤在破旧的窖洞里或干脆就在露天树荫下;没有课桌椅,就坐个马扎,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记笔记;没有教材,授课内容全凭老师的记忆和理解,老师把讲课内容写在黑板上,边讲边让学生抄写。黑板是从老乡那里借来的门板,用刮下的黑锅灰把它涂黑。甚至连自来水笔也没有,就把钢笔头绑在玉米杆上,沾自制的“墨水”。
罗俊才感触很深的还有当时学习用的辞典。那时候整个学校都没有一本中俄辞典,但是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日俄辞典。日语里面会用到汉字,于是全校200多人就通过日语解释里面零星的几个汉字来猜俄语单词的意思。有的时候能够猜对,但是有时中日使用的字意不尽相同,猜错了,闹了笑话。
在极为严峻的对敌斗争中,生存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学习的时间大大受到挤压。1941年,延安遭受了敌军的四面封锁,物资供应极其困难。当时的学习模式是边生产边学习,开荒、种地、缝衣服、挖窑洞都要学生自己动手,这极大挤压了本已不充裕的学习时间。罗俊才回忆,他在延安从1941年到1945年共住了四年时间,学俄语至多两年,占了一半时间,另一半时间用于生产劳动和政治运动。在两年学业中间还穿插着生产劳动。比如,开荒下种后到生长出来有一段农闲时间,这时候上课。过后要上山除草,课就得停下来。七十多年的时光过去了,可罗俊才手上的老茧依然没有褪掉,当时劳动的艰辛可见一斑。
苦中作乐巧学习
艰苦的学习环境虽然不尽人意,学习的时间也非常有限,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依然高涨。不管是教员还是学生,总会在有限的条件中找出更多学习俄语的好方法。罗俊才回忆了许多当时充分利用时间学习的小窍门。
出操是每日的必修课,于是教员带着学生们用俄语喊操。日复一日地重复,单词自然就会入脑,口令里面的那几个词就再也不会被忘掉了。
上山下山的生产劳动在体力上挑战着学生们的极限,但是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却丝毫不减。背粮路上,每个人找一张小纸片,写几个单词或句式贴在后背,让后面的人记。山上劳动时,教员也结合生产劳动,编写一些相关的生词和句子写在小黑板上,供大家在食堂吃饭时记忆,饭后上山把小黑板提上,挂在树上,休息时大家念一念,练一练,充分利用劳动间隙学习。
同学们之间的情谊也让罗俊才感触很深。当时学习全靠自觉,同学们互相督促,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,不让一个人掉队。下课后,同学们会相互对笔记,补充上课没有记录下的内容,在交流中互相促进和提高学习。为了创造语言环境,同学们互为语伴,练习对话。当时每周仅发二两麻油点灯,为了节省使用,同学们只是在睡觉铺床时点一下灯,睡下即吹灭。所以对话练习一般安排在晚上没有灯的时候,白天做书面作业。虽然是在纸张比较匮乏的年代,但是每个人仍然要制作一个非常简陋的单词本带在身上,种地的间隙、上厕所方便的时候,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时间去背单词。同学之间也经常相互考查,开展小竞赛,相互敦促。
都说美剧是练习英语听力和口语的利器,俄语也是如此。那时候会有一些苏联的电影送到延安革命区,这些片子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生活的同时,也成为了他们不错的教辅资料。
革命精神促成长
整个采访过程中,罗俊才提到最多的就是信仰和精神的力量,这也是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支撑起第一代北外人的最重要力量。“当年的学习全靠自觉,但是很少有人偷懒。这是因为到延安学习这个机会对于学生来说无比宝贵,学生也对此倍加珍惜。更是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革命理想,为着共产主义而奋斗。”罗俊才说到这些,依然十分激动。
的确,尽管时代在改变,但是理想与信念的作用,却依然无法替代。在罗俊才身上,我们看到了精神的无穷力量。时至今日,罗俊才依然记得,毛主席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上写到的“勇敢、坚定、沉着,向斗争中学习,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。”,他也时刻牢记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: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。他觉得,校训是留给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,今天依然有着无比鲜活的生命力。
罗俊才毕业之后成为了一名红军军事翻译,后来又与教育结缘。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他,依然保持着每天锻炼读书的习惯。他说,他的一生只做了三件事:一、打日本,救中国;二、充实自己,努力学习;三、从事外语教育,培养人才。从他的回忆中,我们不仅看到了早期外语教学的基本面貌,更看到了第一代北外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信念。这种精神和信念生生不息、历久弥新,将鼓励一代又一代北外人做出更大的成就。
(记者 彭澍 通讯员 袁舒)